11月18日,新加坡证券交易所迎来一位来自长江之畔的“熟面孔”——扬子江海事发展有限公司(股票简称“YZJ MARITIME”,股票代码“8YZ”)以介绍方式正式挂牌交易,成为扬子江船业集团体系内第三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企业。
挂牌上市期间,扬子江海事同步通过私人配售方式成功募集资金约52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2841.63万元),配售发行863.8万股普通股,每股配售价与扬子江海事每股发行价均为0.60新元。上市后,扬子江海事预计市值约达20.93亿新元(约合人民币108亿元)。

纵观扬子江海事的从分拆成立与上市过程,可谓是扬子江系一系列资本结构重组、业务身份重构的延续。如果说2007年扬子江船业新交所上市完成了集团“第一次资本化”;2021年前后扬子江金控的成立与扩张奠定了“第二次金融化”;那么扬子江海事的分拆上市,或许正是任元林“第三次造梦”的起点:一个可循环扩张的海事资本帝国雏形已经出现。
扬子江海事:轻运营、重配置
与传统造船企业不同,扬子江海事从诞生第一天起就定位为“海事金融解决方案提供商”,并刻意保持轻运营、重资产配置的结构。
海运圈聚焦此前从扬子江金控相关人士获悉,扬子江海事将专注于海事产业链投资、融资、咨询一站式服务。

投资端,扬子江海事与船东合资下单新造船,通过对造船环节的强势成本管理,将船厂利润压缩到最低,从而最大化资产回报率。如果资产在特定窗口期无法出售,公司也具备短暂自持、投入运营的灵活性,以时间换空间,等待价格回到合适区间。而在二手船投资上,公司同样采取合资结构,借助运营方的管理能力获得稳定现金流,实现轻资产条件下的收益优化。
在融资端,公司扮演的是传统银行不愿涉足领域的“填空者”。它以融资租赁结构承接高龄船等高风险资产,使交易得以成立;在合作船东资本金不足时,它又以股权融资介入,形成股债结合的“混合结构”,既保证项目落地,也提高双方的绑定程度。

至于咨询等一站式服务领域,公司同样发挥金融信用与产业资源的双重优势。凭借在银行体系的信用能力,它能为中小船厂提供保函服务,成为建造交易背后看不见的“信用支柱”;在采购环节,公司通过集采降低成本,再与合作方共享节约所得;在市场向好、租金上涨的阶段,公司则抓住套利窗口,通过转租实现收益最大化。这些看似分散的业务动作,其底层逻辑却高度统一——都是围绕海事资产的生命周期进行价值捕捉。
新平台承载新一轮海事布局
从业务结构来看,扬子江海事并非扬子江金控旗下其他板块的简单延伸,而是承担着集团海事资产配置平台的核心角色。它与传统制造端、金融控股端并不重叠,而是专注于通过资产投资、资产管理与资产处置贯穿海事资本全周期。
在上市前夕,扬子江海事公布了最新的动向:将向一家位于马绍尔群岛的船东出售四艘MR型油轮(49,800载重吨),总价值1.8亿美元。这些油轮正在中国一家造船厂建造,预计将于 2026 年至 2027 年间交付。

此外,扬子江海事已签署意向书,拟与多家船东合资建造八艘船舶,其中包括四艘MR型油轮(49,800载重吨)和四艘灵便型散货船(40,000载重吨)。其中,四艘MR型油轮的建造合同已与一家欧洲船东签署,而四艘散货船的建造合同则已与一家新加坡船东签署。这些船舶将在中国两家造船厂建造,预计将于 2027 年至 2028 年间交付。扬子江海事将持有这些合资企业的大部分股权。
在这轮全球海事资产重构周期中,扬子江海事实际上在做两件非常关键的事。第一件,是在脱碳压力持续升级的大背景下提前锁定一批“现代、环保型”船舶资产。未来5至10年,海事金融最确定的结构性机会,就是由IMO减排法规、欧盟ETS、租家偏好转变所共同驱动的全球船队升级潮。低油耗、新设计、低排放的现代船型,将成为资产价格最稳健、流动性最好的核心资产。扬子江海事的投资方向正精准落在这一趋势上:通过在建订单锁定建造成本,通过与合作船东合资配置新船,通过运营与处置灵活切换来捕捉船队更新中的确定性回报。

第二件事,则关乎公司国际化战略的跃迁——利用新加坡这一全球航运金融中心的生态优势,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海事资产网络。新加坡汇聚着全世界最密集的船东总部、租家、融资机构与资产管理者。扬子江选择将总部与基金团队设在这里,背后不是简单的地理选择,而是战略上的深度嵌入:获取全球项目来源、进入国际航运金融的话语体系,让中国的海事资本以“主流资本”的身份在全球市场中流动。扬子江海事的国际化路径,本质上是扬子江集团整体全球化战略的延伸,它让集团的价值链从“江苏制造”升级为“江苏制造 + 新加坡金融 + 全球资产配置”的三维结构。这是从区域制造企业向全球资本企业迈进的关键一跃。
对于一家从乡镇修船合作社起步的企业而言,能够一路跃升至“全球海事资产管理平台”的高度,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极为稀缺的组织成熟度与战略前瞻性。
扬子江金控,“回归实业”
自2021年成立以来,扬子江金控一直被视为集团最具野心的板块——它曾试图承担“集团内部金融控股公司”的角色,将造船业积累的现金流导入金融投资体系,迅速扩大资产管理规模,并向更广义的金融业务延伸。
扬子江海事的上市,标志着扬子江金控最为核心的海事业务剥离,其将向新的“实体产业投资”方向过渡。

这一转向在近期尤为明显。此前,扬子江金控曾公告将收购杉杉股份,尽管方案最终未获债权人组通过,但其试图接手一家新能源材料巨头的动作释放出明确信号:扬子江金控不再满足于资本层面的“抽象收益”,而是重新寻找新的实体资产,试图将其在造船业的运营效率、管理能力与资本配置逻辑复制到更广阔的制造业领域。
这一收购意图揭示了一个趋势:扬子江金控正在押注下一轮中国制造业结构性升级的深层机会。它所关注的,不再是传统海事资产,而是中国供应链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领域的长期成长性。杉杉破产重整未能落地,并不意味着扬子江金控的资本野心被遏制,相反,这种跨行业探索表明集团正在寻找新的增长坐标,试图在全球供应链重塑的窗口期实现新一轮产业延伸。

因此,分拆扬子江海事并非简单的业务切割,而是扬子江金控“去金融化、回实体化”的关键节点。通过将海事资产、船舶投资、融资租赁等业务划归独立平台,金控本体得以卸下金融属性更强、监管限制更多的资产结构,转而专注于战略性实业投资。表面上看,这是一次“瘦身”;但从长周期看,这是金控未来扩张的前置条件,只有在资本结构更轻、战略聚焦更明确的前提下,扬子江金控才能真正踏入下一个产业赛道,在集团层面完成从造船企业到“复合型产业资本体”的进化。
任元林:三个时代、三次转身,一个资本帝国的雏形
事实上,无论是扬子江船业、扬子江金控,还是最新的扬子江海事,都离不开其背后的核心灵魂人物——任元林,一个从焊工岗位起步、从学徒身份走出的企业家,他的个人轨迹几乎与中国民营造船业的发展脉络同步。他既是产业周期的亲历者,也是周期节点的洞察者,更是扬子江船业能在风暴中屡屡踩点成功的关键变量。从他的职业路径往回看,是三个清晰的时代、三次关键的转身,而今天的扬子江海事与扬子江金控,正是这三次转型共同作用的资本化结果。
第一阶段是“技术破局”。1975年,年仅18岁的任元林走进扬子江船厂,先做焊工,再学设计,随后转向管理,又在缺乏资源的年代自学英语。他最终成为厂里少见的“复合型人才”:能看懂英文图纸、能与海外船东交流、能在一线解决技术问题。1986年,他成为公司对外接触的关键人物,代表船厂前往新加坡洽谈项目,而到了1997年,在船厂订单几乎归零的危机关头,他被推至台前,接任厂长。这个阶段的任元林,是典型的“技术—运营型”领导者,深谙造船工艺、理解国际标准,也能从市场端反推生产端的改造方向。

第二阶段是“体制破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东亚制造业,全球船市进入寒冬,国企体制下的扬子江面临更深的束缚。任元林在此背景下推动改制,将扬子江彻底从国有体系中剥离出来。这是中国造船史上第一次有国有船厂彻底民营化,并由改制后的团队自负盈亏。这一决定让扬子江在周期底部抢先完成体制脱胎换骨,此后数年,公司销售额迅速突破10亿,利润达到1.5亿;2005年,新扬子造船开建;2007年新加坡上市,募资超百亿元;又凭借充足现金与信誉获得500亿元无抵押授信,并在韩国几乎垄断的高端船型中撕开缺口。这个阶段的任元林,已从技术型厂长成长为具备组织塑造力与战略判断力的产业领军者,是“体制与规模能力”真正迸发的时期。
第三阶段则是“资本破局”,也是任元林对产业边界进行重定义的阶段。自2008年以来,随着全球航运金融的重组与资本市场的深化,他逐步从制造业转向资产管理维度:通过投资与并购扩张船厂产能;介入海事金融领域,形成完善的融资租赁与资产配置架构;推动扬子江金控的诞生,使其不仅作为融资平台,更是产业资本的母体;最终到今天,再将扬子江海事独立拆分上市,进一步构建拥有投资、融资、租赁与运营闭环的海事资本平台。任元林的角色,也在这一过程中悄然完成升级——从“造船企业家”转向真正意义上的“海事金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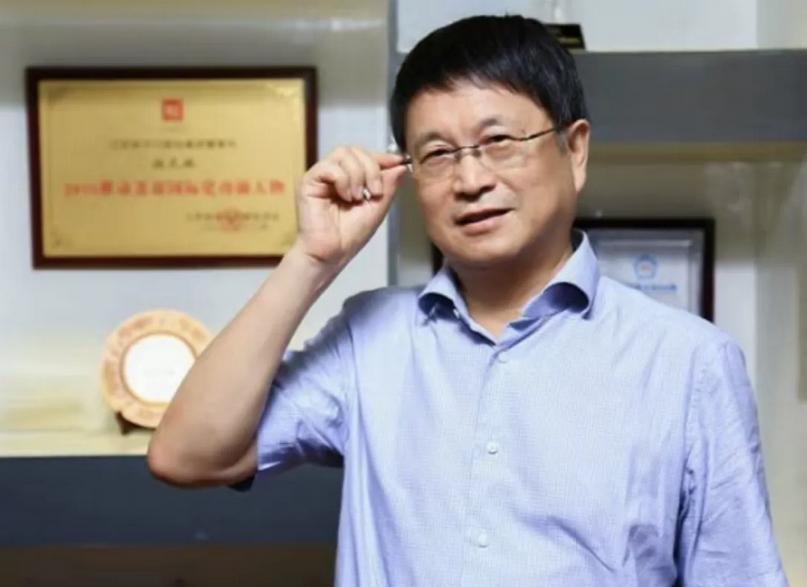
扬子江海事上市,不过是这条资本路径中的又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它不仅意味着船厂制造能力向海事资产管理能力的延伸,更意味着任元林所构建的海事资本帝国第一次具象化、结构化地呈现在市场面前。
三个时代,三次转身,一个关于产业资本化的雏形已经成形,而这个帝国的底层逻辑,正是任元林过去五十年穿越周期、打破边界、不断自我进化所积累的全部经验与判断力。
资料来源:海运圈聚焦

 2025-11-23
2025-11-23 184
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