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国际海事组织(IMO)主导的“净零框架”本应成为航运业低碳转型的里程碑式协议,却因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反对陷入实施困境。2025年8月13日,美国正式否决该框架并威胁对支持国采取“报复”措施,这一行为不仅撕裂了全球航运减排的多边合作基础,更将对行业规则体系、技术演进路径、市场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国际治理理论与产业经济学视角,系统剖析特朗普政府反制举措的动因及其对航运业的多维冲击,并探讨全球航运业在治理裂痕中的突围路径。

一、政策博弈:特朗普政府反制立场的深层逻辑
特朗普政府对IMO净零框架的抵制并非偶然,而是其“美国优先”政策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延续,背后蕴含着产业利益维护、技术路径主导权争夺与国际规则话语权博弈的多重逻辑。
从产业利益维度看,美国航运及关联产业的现实成本压力构成直接动因。特朗普政府在声明中明确指出,框架要求的“尚未形成全球供应规模的昂贵燃料”将推高运营成本,而对液化天然气(LNG)、生物燃料等美国优势技术的限制,实质是对本土能源产业竞争力的削弱。数据显示,美国是全球第三大LNG出口国,2024年航运业LNG消费量中美国供应占比达32%,若框架禁止此类燃料使用,将直接冲击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能源巨头的市场份额。同时,美国零售业与制造业高度依赖远洋航运,2024年通过海运进口的消费品占比达68%,特朗普政府担忧排放定价机制将通过供应链传导至终端消费,加剧国内通胀压力,这与其关税政策中“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宣称形成表层逻辑自洽。

从技术路径看,美国的反对折射出全球航运脱碳路线的根本分歧。IMO净零框架的核心是通过燃料标准升级(如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推广氨燃料、氢燃料等零碳选项)与排放定价机制(类似“碳关税”的跨境调节)强制推动转型,这与美国主张的“渐进式技术替代”形成对立。美国能源部2024年发布的《航运脱碳战略》明确将LNG、生物燃料列为“过渡性核心技术”,计划到2030年实现航运业15%的减排目标,而非IMO框架要求的25%。这种差异的本质是技术主导权的争夺:美国在LNG产业链(从开采到运输)的技术成熟度与成本优势全球领先,而零碳燃料技术仍处于试验阶段,各国尚未形成绝对优势,美国试图通过延缓规则实施巩固现有技术壁垒。
从国际治理维度看,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实质是对多边规则体系的解构。IMO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其决策机制基于“协商一致”原则,美国的否决与“报复”威胁打破了这一惯例,将单边主义引入全球航运治理。历史上,美国曾通过主导《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等规则塑造航运业标准,但此次反制标志着其从“规则制定者”向“规则破坏者”的角色转变。这种转变与特朗普政府在气候领域的一贯立场一致——2017年退出《巴黎协定》、2023年否决全球塑料污染治理协议,均体现出对“国际规则不得损害美国经济主权”的极端坚持。

二、规则裂痕:全球航运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风险
IMO净零框架的搁浅可能引发全球航运规则体系的“多米诺效应”,从统一标准的瓦解到区域化规则的兴起,航运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治理碎片化挑战。
(一)多边规则权威性的消解与合规成本激增
IMO自1958年成立以来,通过制定统一的安全、环保规则,成为全球航运业的“规则中枢”,其标准被176个成员国普遍接受,形成“一次制定、全球适用”的高效治理模式。净零框架作为首个覆盖全行业的强制性减排协议,本应进一步强化这一权威,但美国的否决使其面临“生效即失效”的尴尬。若框架在10月会议上因美国抵制而无法通过,或通过后因美国报复威胁导致多数国家不敢执行,将直接削弱IMO的规则公信力。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组织规则的有效性取决于“核心大国”的遵从度——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美国拒绝签署,导致深海采矿等条款长期无法落地,这一先例可能在航运减排领域重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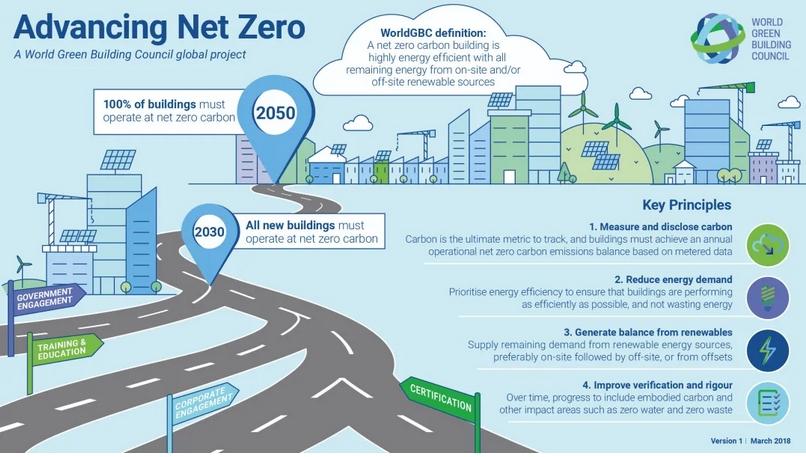
规则碎片化将直接推高航运企业的合规成本。目前,全球80%以上的商船已适应IMO统一标准,若各国因美国反制而各自制定减排规则,船舶将面临“一国一策”的监管困境。例如,欧盟可能坚持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对航运排放征税,中国或推动基于“绿色船舶证书”的港口优先靠泊制度,美国则可能对使用零碳燃料的外国船舶加征关税。这种“规则迷宫”将使航运企业的运营成本上升15%-20%(国际航运公会2025年测算),尤其对中小型航运公司构成生存压力。
(二)区域化规则的兴起与贸易壁垒的隐性强化
美国的反制可能加速航运减排规则的“区域化”趋势,形成以欧盟、北美、亚太为核心的三大规则板块。欧盟作为IMO净零框架的主要推动者,已明确表示“若IMO框架失效,将通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将航运业纳入监管”,计划2026年起对进出欧盟港口的船舶征收碳税。美国则可能联合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自贸区国家,推出基于LNG燃料的“低排放替代标准”,并通过《美国清洁能源法案》对使用该标准的船舶给予关税优惠。亚太地区国家态度分化:日本、韩国倾向跟随IMO框架,印度、印度尼西亚则可能因担忧成本而选择观望,中国或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区域性绿色航运标准,形成独立于欧美的规则体系。

区域化规则的实质是隐性贸易壁垒。美国威胁对支持IMO框架的国家实施“报复”,可能表现为对来自这些国家的船舶加征“碳调节关税”,或限制其进入美国港口。这种“以规则为武器”的贸易保护主义,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形成呼应——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对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已升至12.3%,若叠加航运减排相关的歧视性关税,将进一步扭曲全球贸易流向,导致“近岸外包”“区域供应链”等趋势加剧。
三、产业重构:航运业低碳转型的路径分歧与市场分化
特朗普政府的反制不仅延缓了全球航运减排进程,更将引发行业技术路径、市场格局与竞争规则的深度重构,短期内的混乱或将为长期的差异化发展埋下伏笔。
(一)技术路径的“分叉”:渐进改良与激进转型的博弈
IMO净零框架的核心技术逻辑是“激进式替代”:通过强制标准推动航运燃料从化石能源(重油、柴油)向零碳能源(绿氨、绿氢、甲醇)跨越,预计到2030年零碳燃料占比需达到30%,2050年实现100%。这一路径需要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国际能源署(IEA)测算,仅全球港口加注设施改造就需投入1.2万亿美元。而美国主张的“渐进式改良”则强调依托现有技术:通过提升LNG燃烧效率、推广生物燃料混合比例(如B20生物柴油)实现阶段性减排,到2030年将碳排放强度降低15%,避免因技术跳跃导致的产业震荡。

两种路径的博弈将导致航运业技术研发的“双轨制”。支持IMO框架的欧洲企业(如马士基、地中海航运)已加速布局零碳燃料船舶,马士基计划2027年推出首艘甲醇动力集装箱船,地中海航运则与壳牌合作建设氨燃料加注网络。而美国航运企业(如美森航运、以星美国)更多聚焦LNG动力船舶升级,2025年新下单的船舶中80%仍采用LNG动力系统。这种技术分化可能导致“锁定效应”:选择LNG路径的企业未来若转向零碳燃料,需承担更高的改造成本;而选择零碳路径的企业则面临当前燃料供应不足的现实困境——2024年全球绿氨产量仅能满足航运需求的5%,短期内依赖高价燃料将削弱其市场竞争力。
(二)市场格局的分化:区域化主导与全球化收缩
航运业的市场格局历来与贸易流向高度绑定,规则碎片化将加速市场的“区域化切割”。在欧盟市场,船舶若要进入鹿特丹、汉堡等核心港口,需满足严格的排放要求,这将倒逼往返欧洲的航运企业加速低碳转型,形成“欧洲航线绿色溢价”——即使用零碳燃料的船舶运费较传统船舶高10%-15%,但可规避碳税与港口限制。而美国市场可能成为“高碳船舶避风港”,依赖美国进出口的航运企业更倾向选择LNG动力船舶,以降低合规成本,这将使跨太平洋航线呈现“低碳欧洲段”与“高碳美洲段”的分化。

市场分化还将体现在航运企业的竞争策略上。大型跨国航运公司(如马士基、中远海运)可能采取“多标准适配”策略,针对不同区域市场配置不同技术标准的船舶,例如为欧洲航线配备甲醇动力船,为美国航线保留LNG动力船。而中小型企业由于资金有限,可能被迫退出跨区域市场,转向单一区域运营,导致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2024年全球前20大航运公司已控制78%的运力,若规则碎片化持续,这一比例可能在2030年升至90%以上。
(三)投资逻辑的重构:政策风险主导下的资本再配置
航运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决策高度依赖政策稳定性。特朗普政府的反制与IMO框架的不确定性,将使行业投资逻辑从“技术前景驱动”转向“政策风险规避”。国际航运公会(ICS)2025年调查显示,62%的航运企业推迟了2025-2030年的船舶更新计划,其中78%的企业将“政策不确定性”列为首要原因。

资本流向的分化尤为明显。支持IMO框架的国家和企业更倾向于获得绿色金融支持——欧盟“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SFDR)已将航运减排项目列为优先投资领域,2024年欧洲绿色债券中航运相关占比达18%。而美国市场的投资更多流向传统能源与现有技术改造,2025年美国能源部对LNG船舶技术研发的补贴预算增至12亿美元,较2024年翻倍。这种资本分化将进一步拉大不同技术路径的差距,使“低碳俱乐部”与“高碳阵营”的边界愈发清晰。
四、破局之道:全球航运治理的协同路径与产业转型的平衡策略
面对特朗普政府反制引发的治理裂痕与产业困境,国际社会需从规则重构、技术协同、利益平衡三方面探索破局之道,推动航运业在分歧中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一)构建“多层次治理体系”,缓解规则碎片化
短期内,完全统一的全球规则难以实现,可建立“IMO框架+区域补充+行业自律”的多层次体系。IMO可将净零框架拆分为“核心条款”与“自愿条款”:核心条款保留全球统一的减排目标(如2050年净零),自愿条款允许各国根据技术水平选择过渡期措施(如美国可保留LNG作为过渡燃料,但需承诺2035年前逐步退出)。区域层面,欧盟、亚太等可建立“规则互认机制”,避免重复监管——例如中欧可协商将欧盟ETS与中国“绿色船舶评价体系”对接,实现碳排放数据互认。行业层面,国际航运公会可推动企业签署《自愿减排承诺书》,通过行业自律弥补政府间合作的不足。

(二)推动“技术协同创新”,降低转型成本
技术路径的分歧本质是成本与效率的权衡,需通过国际合作降低转型门槛。可建立“全球航运脱碳技术联盟”,由IMO牵头,整合欧美、中日韩等国的研发资源,重点突破零碳燃料生产(如绿氨电解技术)、船舶动力系统改造(如氨燃料发动机)、碳排放监测(如卫星遥感监测)等关键领域。同时,设立“航运脱碳基金”,由发达国家与大型能源企业出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移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例如美国可通过基金输出LNG清洁利用技术,换取对零碳燃料研发的参与权,实现技术路径的渐进融合。
(三)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平衡各方诉求
美国的核心关切是短期成本压力,可设计针对性的补偿措施:IMO可设立“过渡期豁免条款”,允许美国等国家在2030年前对LNG燃料船舶给予排放核算优惠,但需将节省的成本投入零碳技术研发;同时,全球排放定价机制可设置“梯度收费”,对发展中国家与转型期国家降低费率,避免单一标准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此外,可将航运减排与贸易政策挂钩,例如对遵守IMO框架的国家给予关税优惠,通过利益激励引导美国重新参与全球合作。

特朗普政府对IMO净零框架的反制,是全球气候治理中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博弈的缩影,其影响远超航运业本身,折射出多边合作体系在单边主义冲击下的脆弱性。尽管短期内规则碎片化、技术分化、市场割裂难以避免,但航运业作为全球化的核心基础设施,其低碳转型的大方向不会因单一国家的抵制而逆转。未来,全球航运业的发展将呈现“在分歧中协同、在协同中转型”的特征:规则层面从“一刀切”转向“灵活适配”,技术层面从“路径对立”转向“协同融合”,利益层面从“零和博弈”转向“共担共享”。唯有如此,才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与产业转型的现实性之间找到平衡,推动航运业真正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资料来源:海运圈聚焦

 2025-11-01
2025-11-01 322
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