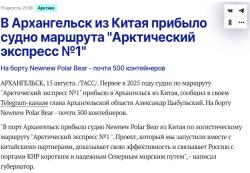未能交付货物和拒收货物是商品价格波动常导致国际贸易合同中最常见的两种违约形式。拒收货物的可以参考早先Sharp Corp Ltd v Viterra BV [2024] UKSC 14案;买方为未付货物,卖方转售货物。未能交付货物计算损失通常参考“可供交易市场”- available market的价格为基础,初步衡量损失。在国际贸易中,确定构成“可供交易市场”(建立市场损失的前提)的标准是一项多因素考量。无辜方是否需要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便宜的替代货物以证明其已尽减损义务?这些问题在新加坡高等法院最近的判决Shri Bajrang Power and Ispat Ltd v Steel Corp Ltd [2025] SGHC 107案中进行了解释。
在本案中,原告印度钢铁制造商Shri Bajrang Power and Ispat Ltd(与被告英国金属贸易商Steel Corp Ltd在2023年7月17日签订合同,以381美元/吨的价格购买30,000吨生铁用于钢铁生产,预计2023年8月15日从土耳其黑海中的港口装运到印度的Vizag港。
然而,被告未能在2023年8月15日前装运用于炼钢的生铁。六天后,即8月21日,原告致函被告,通知其约定的发货日期已过,并要求被告尽快指定运输船舶。被告于次日(8月22日)回复,解释称延误是“由于黑海地区不可控情况”导致,并向原告保证正在努力履行合约。2023年9月14日,被告告知原告其准备供应炼钢生铁,但价格提高至每吨420美元。一周后,即9月21日,被告通知原告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其无法履行合同。原告随后于2023年9月25日向被告发出索赔函,被告同日回复,称此事不再有进一步追索权。双方同意,合同于2023年9月25日终止。
由于被告未能交货,原告转而使用钢屑(即炼钢中生铁的替代品)进行钢铁生产;在2023年9月至2024年8月间从印度市场购买了28,817吨钢屑。原告于2024年7月12日提起诉讼,并因被告未能在2024年12月4日提交是否抗辩的通知而获得缺席判决。本判决涉及根据该缺席判决评估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损害赔偿。原告主张,其有权根据《1979年货物销售法》(2020年修订版)第51(3)条获得赔偿,或备选根据第51(2)条获得赔偿,因为该合同符合该销售法案第2(1)条定义的“货物销售合同”。相关条款如下,第51条:
(1) 若卖方错误地疏忽或拒绝向买方交付货物,买方可对卖方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未能交货的损失。
(2) 赔偿的衡量标准为卖方违约在正常情况下直接且自然导致的估计损失。
(3) 若存在货物相关的可供交易市场,赔偿初步以货物应交付时(或若未规定时间,则拒绝交付时)的市场价格或当前价格与合同价格之间的差额确定。
51.(1) Where the seller wrongfully neglects or refuses to deliver the goods to the buyer, the buyer may maintain an action against the seller for damages for non-delivery.
(2) The measure of damages is the estimated loss directly and naturally resulting,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events, from the seller’s breach of contract.
(3) Where there is an available market for the goods in question, the measure of damages is prima facie to be ascertained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ract price and the market or current price of the goods at the time or times when they ought to have been delivered or (if no time was fixed) at the time of the refusal to deliver.
本案涉及土耳其至印度的国际货物销售,双方来自不同海外司法管辖区。合同明确规定,任何因合同产生或与之相关的争议适用英国法,并由新加坡法院享有专属管辖权。上诉法院认为,严格来说,《1979年货物销售法》不应适用于明确规定适用英国法的国际合同。然而,双方均未就外国法的适用性提出意见,而是假设《1979年货物销售法》条款适用。上诉法院认为无论本案适用《1979年货物销售法》、英国《1979年货物销售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还是普通法原则,结果可能相同;因为赔偿和减损的合同原则在这些法律框架中是共通的。
《1979年货物销售法》条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普通法关于违约赔偿的立场。这在Bunge SA v Nidera BV [2015] 2 Lloyd’s Rep.469, [2015] UKSC案第16段中明确, Sumption勋爵在提及英国《1979年货物销售法》第51(2)-(3)条(与该法案第51(2)-(3)条内容一致)时,认为第51(2)条在卖方未能交货的背景下规定了赔偿原则。第51(3)条规定了存在可用市场时的初步赔偿衡量标准,但与其说是一项规则,不如说是一种初步满足第51(2)条一般原则的技术。
原告援引Swiss Singapore Overseas Enterprises Pte Ltd v Exim Rajathi India Pvt Ltd [2010] 1 SLR 573案,该案涉及因买方违约导致卖方应得的赔偿评估。在案中第[66]段阐述了《货物销售法》(1999年修订版,第393章)第50(2)和50(3)条的交互作用,这与《1979年货物销售法》第51(2)和51(3)条相对应。因此,原告主张,这些原则应适用于因卖方违约导致买方应得的赔偿评估。因此,若存在可用市场,适用《1979年货物销售法》第51(3)条;若无可用市场,则适用第51(2)条的一般原则。
高等法院认为,“可供交易市场”-available market,指买方和卖方的存在及其随时供应或吸纳相关货物的能力(参见Marco Polo Shipping Co Pte Ltd v Fairmacs Shipping & Transport Services Pte Ltd [2015] 5 SLR 541案第[30(b)]段)。这是一个事实探究,取决于产品性质、涉及数量、供应来源、时间框架、价格及价格变动(参见Panwah Steel Pte Ltd v Burwill Trading Pte Ltd [2006] 4 SLR(R) 559案第[34]段。
双方不争执存在“可供交易市场”,且相关期间为2023年9月14日至25日。被告同意原告对《1979年货物销售法》第51(2)和51(3)条的分析。上诉法院认为尽管法院认可存在可用市场,但减损原则影响本案赔偿的计算方式,使得《1979年货物销售法》第51(3)条不适合作为赔偿衡量标准。尽管如此,法院将处理双方对《1979年货物销售法》第51(3)条的意见。
原告律师主张,印度市场构成相关“可供交易市场”。这一观点得到双方联合专家的证据支持,专家认为印度生产商提供的生铁数量足以构成原告的可行供应来源。相反,被告律师主张,“可供交易市场”包括外国生铁来源(包括南非和俄罗斯),不包括印度市场。基于此,被告律师认为,原告完全无权获得赔偿,因为其选择从印度购买钢屑而非更便宜的海外生铁是不合理的决定,完全未能减轻损失。
被告援引The Asia Star [2010] 2 SLR 1154案第[22]–[24]段,主张无辜方有义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减轻因违约方违约导致的损失,且无法就其因自身不合理行为或不作为未能避免的损失获得赔偿。被告依据其专家的报告,指出相关期间印度市场生铁价格为每吨468.51美元,远高于南非(每吨371.77美元)和俄罗斯(每吨397.03美元)的生铁价格。被告强调,南非生铁价格甚至低于合同价格(每吨381美元)。因此,被告律师认为,原告没有理由从印度供应商采购。
原告反驳称,减轻损失的义务不要求以牺牲商业合理性为代价追求最低价格,也不要求“满世界寻找”替代货物(参见The Asia Star案第[47]段)。原告解释,其炼钢炉持续运行以生产多种钢产品,因此不间断的原材料供应至关重要。此外,原告一直从印度市场采购生铁,本合同是其首次尝试从国外购买生铁。专家报告还指出,印度是“生铁生产大国”,2022年印度生铁进口仅占其总消费量的0.12%,表明印度基本自给自足,国内采购是标准做法。因此,原告认为,从印度市场寻找替代品非常合理。
被告回应称,原告所谓及时原材料供应的需求缺乏依据,其索赔函中无证据显示这种紧迫性。此外,原告在合同终止近一个月后才采购钢屑,这削弱了其紧迫性的主张。被告还称,原告明知选择更昂贵的本地供应商以确保供货稳定性,现在试图向被告追偿这种自愿承担的“溢价”。
高等法院认为,根据《1979年货物销售法》第51(3)条确定“可供交易市场”时,必须从买方角度考虑,不仅考虑货物的理论可用性,还需考虑买方面临的商业现实。尽管被告正确指出存在价格更低的外国生铁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原告角度看,这些来源属于相关可用市场。
基于上述理由,高等法院认为印度市场是更合适的“可供交易市场”。证据显示,原告迅速采取行动解决问题,首先要求加快交货,随后寻找生铁的替代品。索赔函用于通知被告其违约并要求履行,同时明确保留原告的权利和救济。从被告最终拒绝履行到原告采购替代货物之间的时间段,考虑到原告需要评估选项和安排替代方案,也是合理的。
高等法院认为,减损义务有其限度,合理性探究最终是一个事实问题。在本案中,从印度市场采购替代品在商业上是合理的。印度与外国生铁来源之间的价格差异需结合海外采购的额外风险和不确定性来考量。这些风险包括潜在的运输延误、海关清关问题以及与不熟悉的供应商交易的不确定性。被告将此称为自愿承担的“溢价”未抓住重点。所谓的溢价反映了供应确定性和可靠性的真实商业价值。正如本案所示,原告与新的海外供应商交易带来了成本。因此,在被告违约后,原告选择本地替代品完全合理。
然而,高等法院认为,基于印度市场生铁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额计算赔偿将使原告获得超过其实际损失的赔偿。合同终止后,原告作出商业决定,购买钢屑作为生铁的替代品。钢屑价格高于合同生铁价格(每吨381美元),但低于印度市场生铁价格(每吨468.51美元)。无辜方不得就其通过减轻损失避免的损失获得赔偿。由于原告以低于印度市场生铁价格的价格购买钢屑,这种减轻损失行为应作为计算赔偿的基础,而非理论上的市场价格差额。
高等法院认为这一立场得到Bunge SA v Nidera BV [2015] 2 Lloyd’s Rep.469, [2015] UKSC 43案的支持。Sumption勋爵在17段判决书中认为,若存在货物可供交易市场,市场价格以合同交付日期确定,除非买方应在更早阶段进入市场签订替代合同以减轻损失:参见Garnac Grain Co Inc v HMF Faure & Fairclough Ltd [1968] AC 1130案和Tai Hing Cotton Mill Ltd v Kamsing Knitting Factory [1979] AC 91案。通常,受损方需在原合同终止后合理时间内进入市场签订替代合同,赔偿将根据其获得的价格评估。若其选择不这样做,赔偿通常以其应采取行动时的市场价格为准:参见The Elena d’Amico[1980] 1 Lloyd’s 75案。结果是,在存在违约和可供交易市场的情况下,评估赔偿的有关市场价格通常不由初步衡量标准决定,而是由减损原则决定。
原告主张,即使《1979年货物销售法》第51(3)条的赔偿衡量标准不适用,估计损失仍应以印度市场生铁现行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额计算,以补偿原告因无法以印度现行价格转售炼钢生铁而损失的利润。原告称,以低于印度市场生铁价格的合同价格转售生铁完全合理。尽管被告未对此提出意见,上诉法院不认同这一推理,因为原告是钢铁生产商,无证据显示其从事生铁转售业务。原告的解释似乎试图为其超出实际损失的赔偿主张提供理由。
因此,高等法院认为原告仅应就其因从印度购买钢屑而产生的损失获得赔偿。使用钢屑涉及购买煅烧石油焦和冶金焦以获取碳素,而这些碳素原本可从生铁获得。综合考虑使用钢屑替代生铁的所有成本,生产成本每吨约增加35美元。对于替代30,000吨炼钢生铁,总计损失为1,050,000美元。因此,原告应获判赔偿1,050,000美元及利息。
总结:
首先,本案中的第一个焦点争议是何为“可供交易市场”。《1979年货物销售法》(Sale of Goods Act, SGA)第51条(3)条规定,若存在货物相关的可供交易市场,损害赔偿应通过合同价格与该市场当前价格的差额确定。这引发了本案双方对“可供交易市场”解释的问题。核心问题是买方在商业背景下可随时购买相同类型替代货物以满足需求的地点。上诉法院解释称,这是一个事实特定问题,需从买方(即原告)的角度确定。原告主张,印度市场而非全球市场是相关的“可供交易市场”。相反,被告则认为,“可供交易市场”应包括俄罗斯和南非等更便宜的海外来源,若原告利用这些来源,原告的损失风险会降低。
高等法院支持了原告的主张,认定可供交易市场为印度市场,而非全球市场。原因在于,原告在短时间内从印度市场采购是合理且常见的做法。关键考量因素是替代货物的可用性和可得性。从实际角度看,高等法院分析,买方在卖方违约后需在合理时间内以一定供货保障采购替代品。印度(本地)市场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转向合理减轻损失:评估损害赔偿的相关性在存在可用市场的情况下,损失为市场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额,但这一理论损失仅是起点,法院需审查无辜方是否已减轻损失并实际遭受损失。法院援引英国案例Bunge SA v Nidera BV案。在该案中,英国最高法院裁定,通常情况下,即使存在可供交易市场,“受损方需在原合同终止后合理时间内进入市场寻求替代合同以减轻损失。赔偿将根据其获得的价格评估”。该案还进一步指出,实践中,若一方选择不减轻损失,赔偿通常以其应采取减轻措施时的市场价格为准。因此,评估赔偿的有关市场价格通常由减损原则决定,这与无辜方减损的义务一致。
最终,高等法院未基于生铁的假设市场价格(比合同价格高约80美元/吨)裁定赔偿,而是考察原告实际产生的额外成本。通过使用钢屑而非昂贵的印度生铁,原告每吨额外成本为35美元以使钢屑可用于钢铁生产。因此,赔偿基于实际生产成本差额,而非理论损失。这反映了普通法律赔偿的基本原则——赔偿旨在补偿,而非奖励。
高等法院还回答了什么是合理减轻损失的问题。法院强调,减轻损失的义务不要求采取非常措施。依据新加坡上诉法院案例The Asia Star,减轻损失义务受合理性原则约束,合理性依事实确定。在本案中,原告选择本地采购钢屑被认为合理,考虑到可靠供应的需求及公司惯常业务实践。法院驳回被告要求原告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低价格(包括俄罗斯或南非)的论点,因为本地采购是标准做法且供货确定性更高。
高等法院认为,合理评估与减轻的赔偿简言之,面对合同违约,受损买方可依据可用市场价格评估损失,这是一种基于商业现实而非假设可能性的评估。一旦损失确定,法律将平衡无辜方采取的合理减损措施。受损买方应专注于实际、商业上合理的减轻损失步骤,同时记录其行动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寻求合理性,而非完美无瑕。
在案中所提到的The Asia Star [2010] 2 Lloyd’s Rep.121案,新加坡的上诉法院认为减损的基本规则已明确。首先,受损方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步骤减损因违约方违约造成的损失,且无法追回因其自身不合理行动或不作为未能避免的损失。其次,若受损方超出法律要求,避免了全部损失,则无权追回任何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受损方的努力实际上为违约方提供了无偿利益。第三,受损方可追回在合理减损措施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简言之,受损方无法追回可避免或已避免的损失,但可追回合理减损措施中产生的费用。评估受损方减损行为的合理性应从违约方违约之日起开始,证明受损方未能履行减损义务的责任由违约方承担。这一证明责任通常不易履行。具体转向因船东未能提供承诺的船舶而导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违约的情况,通常的减损措施包括租船人(在此场景中为受损方)租用替代船舶运输相同货物,或在预定交付地点获取替代货物。租船人只需在决定采取哪种替代措施时合理行事即可。然而,通常情况下,其应选择成本最低的选项。一般而言,若有合理条款的替代船舶可用,承租人应通过租用该船舶减损其损失。若承租人无法租到与原租船舶相同大小的船舶,其有权选择次佳的合理选项,包括租用更大船舶,若不这样做会导致违约方更大损失。在此需注意,承租人不得以“不谨慎或奢侈的方式”行事。
另外,开头提到的Sharp Corp Ltd v Viterra BV [2024] UKSC 14案,最高法院认为损害赔偿法的两个基本原则是赔偿原则和减轻损害原则。赔偿原则旨在使受损方恢复到若未发生违约责任时的相同地位。对于合同损害赔偿,这意味着受损方“在金钱可以做到的情况下,就赔偿而言,应被置于合同已履行时的相同处境”:参见Robinson v Harman (1848) 1 Exch 850案 Bunge SA v Nidera BV 案。
最高法院认为,减轻损害原则要求受损方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避免错误行为的后果。这意味着:(i) 受损方不得就合理应避免但未能避免的损失获得赔偿;(ii) 受损方可就采取合理减损措施所产生的损失获得赔偿,即使该措施增加了损失;(iii) 若通过采取合理减轻措施成功减少损失,则违约方有权从中受益,即不得就已避免的损失获得赔偿——例如,参见Robert Goff法官在The Elena d’Amico [1980] 1 Lloyd’s Rep.75案第88页的判决。在McGregor on Damages第21版第9.002-9.007段中,这些被描述为减损的“三条规则”。
最高法院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赔偿原则和减损原则共同作用,减损的合理步骤通常确定赔偿性损害的衡量标准。例如,在货物销售中,受损方(卖方)通过合理替代销售或(买方)通过合理替代购买的减损措施通常是可获赔偿的基础。违约条款反映了赔偿原则和减损原则。最高法院认为,赔偿的起点是子条款(a),处理受损方进入市场进行替代销售或购买的情况。正如《1979年货物销售法》第50(3)和51(3)条所确认的,在存在货物可供交易市场的情况下,受损方预计会采取合理减损措施。若双方对替代交易的违约价格(参见子条款(b))无异议,则该价格将确定违约价格,根据子条款(c),应支付的赔偿将是合同价格与违约价格之间的差额。赔偿因此由受损方在减轻损失时采取的合理步骤确定。正如Sumption勋爵在Bunge v Nidera第[32]段所述:“子条款(a)和(b)涵盖了普通法关于减轻因价格变动导致损失的原则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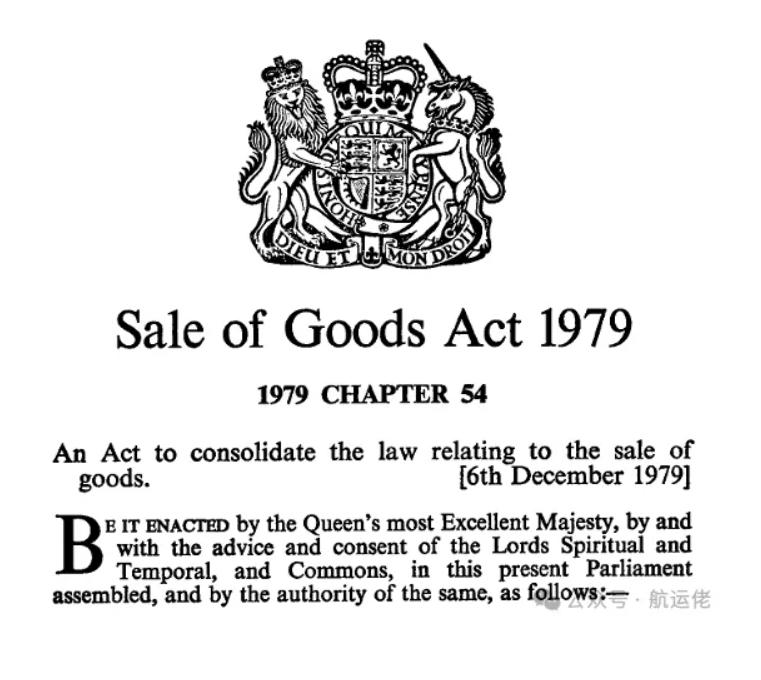
海运圈聚焦专栏作者Alex (微信公众号 航运佬)

 2025-08-22
2025-08-22 399
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