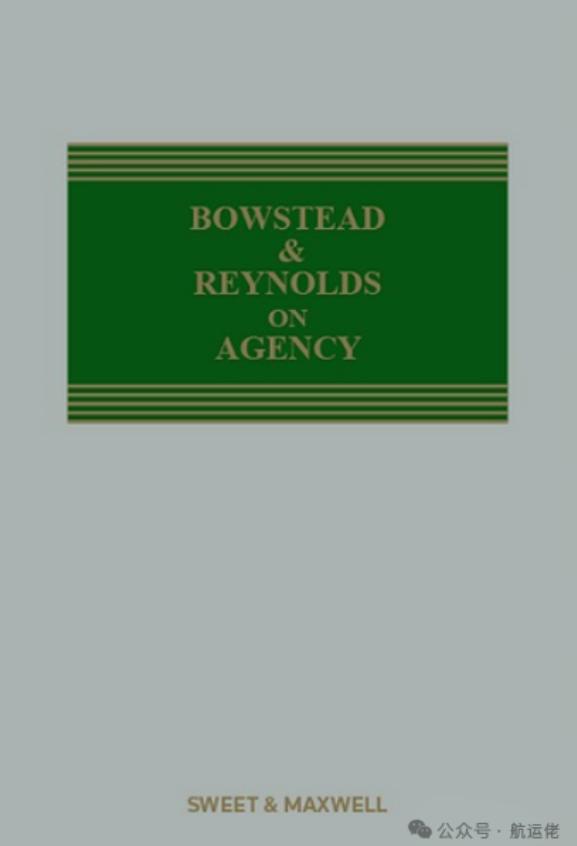
在Berge Bulk Shipping PTE Ltd v Taumata Plantations Ltd & Ors [2025] EWCA Civ 876案中,案件上诉的争议焦点是英国法院是否对船东(两艘船舶的实际所有人)根据两份在印度无单卸货而提供的保函提出的索赔具有管辖权。这些赔保函受英国法律管辖,并规定由英国法院管辖,由一家现已破产的新西兰公司TPT Shipping Ltd(“TPT”)以其名义签发的。英国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取决于是否存在充分的论据支持(good arguable case),证明三个新西兰公司(“Taumata”、“Tiaki”和“OTPP”,统称为“出口商”)作为TPT的未披露委托人应对保偿承担责任。
Christopher Hancock KC法官认为不存在这样的主张,因此英国法院对本案的索赔没有管辖权;船东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
双方当事人及法官分两个阶段处理隐名代理人(undisclosed principals)问题,应用充分的论据支持标准。第一阶段是考虑出口商是否是船舶航次租船合同的隐名代理,这些合同以TPT的名义签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非以委托人身份行事。第二阶段是考虑出口商是否是保函本身的隐名代理。双方一致同意,第二阶段是关键,但每一方都认为其在第一阶段的立场为其在决定性第二阶段的立场提供了支持。
通过回应通知,出口商主张,即使存在充分的论据支持证明他们作为隐名代理人需承担责任,也没有需要审理的实质性问题,因为船东已做出具有约束力的选择,仅向TPT寻求救济,和/或由于其对TPT清算人提出的索赔被接受,其对出口商的索赔权已消灭。法官认为无需处理这些问题,且由于上诉法院同意其关于隐名代理问题的结论,因此关于其他问题的任何评论均为非必要意见(obiter),无需在本判决中讨论。
关于充分的论据支持,双方一致同意,根据《民事诉讼规则》(CPR)6.33(2B)(合同包含法院具有管辖权的条款)确立管辖权所需的测试标准是充分的论据支持(good arguable case)。这一标准的含义在Clifford Chance LLP v Société Générale SA [2023] EWHC 2682 (Comm) 案中由Henshaw法官准确总结如下:
‘79. 主张存在具有约束力的管辖权协议的一方需要证明存在充分的论据支持。实际上,这意味着:
i) 依赖协议存在的一方必须提供证据基础,证明其论点更具优势(但无需明显优于对方)。
ii) 如果存在事实争议或其他理由使人怀疑协议是否适用,法院必须在可信赖的材料基础上做出判断。
iii) 如果争议的性质和临时阶段可用的材料限制使得无法进行可靠评估,则只要存在合理(尽管有争议)的证据基础,就可认为存在充分的论据支持。’
关于隐名代理人规则,上诉法院的Males勋爵认为,代理是一种基于双方同意的关系,需通过客观判断双方同意的存在,正如Garnac Grain Co Inc v HMF Faure & Fairclough Ltd [1968] AC 1130案中所述:
“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只能通过双方的同意建立。如果双方同意在法律上构成这种关系,即使他们自己不承认或明确否认(如Ex parte Delhasse v 7 ChD 511),也会被认为已同意。但同意必须由双方明确或通过言行暗示给予。主要应考察他们在所谓代理关系建立时的言行。早期的言行可作为当时交易习惯的证据,构成历史背景。后期的言行可能也有一定影响,但重要性通常较低。”
尽管未披露委托人规则常被描述为异常,但已确立:以自己名义与第三方订立合同的代理人可使其委托人受约束,因此委托人(以及代理人)既有权根据合同起诉,也需承担合同责任,即使在订立合同时未向第三方披露其代表委托人行事的情况。这一规则的适用情形,Lloyd勋爵在Siu Yin Kwan v Eastern Insurance Co Ltd [1994] 2 AC 199案中认为:
“隐名代理人相关法律的主要特征至少自18世纪末以来已确立。1872年,Blackburn 法官在Armstrong v Stokes (1872) LR 7 QB 598案中表示,关于隐名代理人是否应对代理人代表其订立的合同负责,曾多次引发疑问,但此类疑问现在已为时过晚。
为本案目的,法律可简要总结如下:(1) 隐名代理人可就代理人代表其在实际授权范围内订立的合同起诉或被诉。(2) 代理人在订立合同时必须意图代表委托人行事。(3) 隐名代理的代理人也可就合同起诉或被诉。(4) 第三方对代理人可用的任何抗辩对委托人同样适用。(5) 合同条款可通过明示或暗示排除委托人起诉或被诉的权利。合同本身或合同周围情况可能表明代理人是唯一真正的委托人。”
这一总结在Playboy Club London Ltd v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SpA [2018] UKSC 43案中,第12段中获最高法院认可,Sumption勋爵补充道,第三方必须不可撤销地选择是否起诉代理人或隐名代理人。
Males勋爵认为值得注意的是,Lloyd勋爵的总结明确指出,代理人必须在实际授权范围内行事。Bowstead & Reynolds on Agency(第23版,2024年)第8-070段也持相同观点:
‘代理人必须具有实际授权,以使其委托人对相关交易负有责任或享有权利,该授权可以是明示或暗示的。’
在The Magellan Spirit [2016] EWHC 454 (Comm) 案中,Leggatt法官就相关原则进一步讨论,该案与本案有一定相似性。他提出,存在一种推定,认为合同并非代表隐名代理人订立,只有通过令人信服的证据才能推翻:
‘28.当合同由某一具名法人或为其订立,且合同条款或周围情况未向另一合同方表明具名方作为代理人订立合同时,必须推定具名方是以委托人身份订立合同。这一推定可被推翻,但需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具名方—与表面相反—代表隐名代理人订立合同。’
Males勋爵同意这一分析,但需稍作阐释。隐名代理人规则仅在合同条款或周围情况未表明具名方作为代理人时适用,否则委托人就不算未披露。在这种情况下,起点是具名方非以代理人身份订立合同,但隐名代理人或如本案第三方可尝试证明相反情况。所需证明标准为普通民事诉讼的盖然性权衡标准。Leggatt法官提及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并非要求高于普通民事标准的证明标准(参见他在Tartsinis v Navona Management Co [2015] EWHC 57 (Comm) 案,第84-86段中对“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合同更正背景下的解释),而是反映合同,尤其是正式文件通常为其表面所示。简言之,证明代理关系必须令人信服,因为不令人信服的证据(如果存在)不足以证明合同非表面所示。
Males勋爵也同意Leggatt法官在The Magellan Spirit案中的进一步观点,即要从行为中推断代理关系,必须识别出仅与双方意图由代理人以委托人名义订立合同相一致的行为:
“29. 原则上,必须证明的行为是:(i) 处于代理人地位的合理人会理解其被授权作为代理人代表委托人订立租船合同;(ii) 处于委托人地位的合理人会理解代理人同意这样做。如同任何从行为推断协议的案件,仅指出与代理人作为委托人代理订立合同一致的行为不足以证明协议或双方意图。必须识别出仅与此种协议或双方意图相一致、且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其他意图关系不一致的行为。换言之,如果双方在没有代理关系的情况下可能或确实会如其所为,则推断代理关系将无法成立:参见类似案件,如The Aramis [1989] 1 Lloyd’s Rep.213案和The Gudermes [1993] 1 Lloyd’s Rep.311案。”
法官首先处理对Forests的索赔,认定没有充分的论据支持证明Forests是租船合同或保函(LOIs)的隐名代理人。船东未对这些决定提出异议。至于对出口商的索赔,法官认为出口商的论点更具优势。简言之,他认为TPT在签订租船合同时以委托人身份行事,而非作为出口商的代理人。其核心推理是,代理协议规定当TPT参与时,适用第5.2.1(f)条款,此时TPT以委托人身份行事,而根据第5.2.1(c)条款,Forests则作为出口商的代理人,且这与TPT在不知晓将运载何方货物的情况下签订租船合同的事实一致。
关于保函,法官同样倾向于出口商的论点,在第74段中表示:
“我已认定Forests的论点更优,即保函由TPT以自身名义发出。如果这一结论正确,则该论点不成立,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出口商通过Forests的代理授权了保函的签发。”
Males勋爵认为这似乎是回溯到法官在第64段的陈述:
“基于上述所有理由,我认为船东对Forests没有充分的论据支持证明本法院具有管辖权。因此,对Forests的诉讼应予撤销。”
法官补充道,如果他对Forests的判断有误,代理协议附件2规定了授权保函的特定程序,该程序未被遵循,且若Forests确实授权了保函的签发,其行为未经出口商授权。
船东代表律师承认,法官的决定属于评估性判断,因此若要上诉成功,需指出法官推理中的逻辑缺陷或其他明显错误(参见In re Sprintroom Ltd [2019] EWCA Civ 932案,第76段)。对此,他认为法官在第74段的陈述误解了其在第64段的判决。相反,法官在第64段并未认定保函由TPT以自身名义发出,仅认定没有充分的论据支持证明Forests是TPT的隐名代理人。因此,法官的推理存在缺陷,本法院需自行重新考虑此事。
关于租船合同,船东的代表律师认为船东有更优的论点,证明TPT作为出口商的代理人行事,或者至少存在合理的证据基础支持这一结论。他依赖以下五点主要论据:
(1) 在TPT成立之前,租船合同由Forests作为出口商的代理人签订。
(2) TPT成立后,接替了Forests此前作为出口商代理人的角色。
(3) 《航运服务协议》第5.1条款规定,TPT将代表并为出口商提供服务,这是典型的代理语言。
(4) 资金流向表明,租船合同的经济利益由出口商而非TPT享有:所有运费和滞期费成本均转嫁给出口商,出口商还获得航次收益(如有);甚至地址佣金也归于出口商。
(5) TPT的账目与TPT作为委托人行事不一致:支付给船东的运费及其他费用未在账目中列为支出,出口商向TPT偿还的运费未列为收入,若TPT以委托人身份行事,这些本应如此记录。
船东的代表律师认为,如果存在合理可争议的案件证明出口商是租船合同的隐名代理人,则同样存在充分的论据支持证明他们是保函的隐名代理人,特别是因为保函的签发使出口商受益,避免了因船舶在卸货港延误而需承担的滞期费。
然而,船东的代表律师不得不承认,代理协议附件2规定的程序未被遵循。TPT曾请求批准签发保函,Forests也给予了批准,但未参照出口商意见,违反了规定程序。船东的代表律师试图以两种方式解决这一难题。首先,他认为附件2规定的程序到2019年可能已废弃,因此不再要求遵循,导致Forests有实际授权在不参照出口商的情况下批准保函,因为附件2对其授权的限制不再适用。其次,他援引AJU Remicon Co Ltd v Alida Shipping Co Ltd [2007] EWHC 2246 (Comm) 案中Chambers QC法官的观点,主张只要Forests具有表面或表见授权(apparent or ostensible authority)代表出口商批准保函即可。他最终承认,若要上诉成功,必须在这一点上获胜,而这一点在下级法院未被提出。
Males勋爵认为,首先,他不同意法官误解了他自己判决的观点。虽然严格来说,第74段中法官的陈述(即保函由TPT以自身名义签发)并未完全反映第64段的内容(即没有充分的论据支持证明Forests是TPT的隐名代理人),但通读整个判决,包括法官在第64段对其结论的理由,显然他在处理对Forests的索赔时,确实认为TPT在签发保函时以委托人身份行事。尽管如此,如果法院有权重新考虑此事,Males勋爵认为法官的决定是正确的。
Males勋爵认为,先从租船合同开始分析,尽管最终关键在于保函;但出口商的论点更具优势,即TPT以委托人身份而非出口商的代理人身份签订租船合同。正如已解释,设立TPT的整个目的是使Forests和出口商免于承担作为承租人固有的风险。这一目的与TPT作为出口商代理人签订租船合同的意图不符。在判断出口商是否同意TPT以代理人身份行事时(参见Dinglis Management Ltd v Dinglis Properties Ltd [2019] EWCA Civ 127案,第24及33-35段),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Forests和出口商免于承担船舶承租人义务的隔离措施在代理协议中得以体现,该协议在第5.2.1条款的(c)和(f)项之间划定了明确区分。在后者(涉及TPT)的情况下,不存在代理关系。
在这一清晰的合同背景下,证明TPT在签订租船合同时不应作为出口商的代理人,船东的代表律师所依赖的因素分量甚轻。虽然《航运服务协议》第5.1条款的措辞(代表并为)与代理关系一致,但它并不排除其他关系,因为“为”和“代表”可能具有更广义的“为……利益”的含义(参见Rochdale 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 v Dixon案 [2011] EWCA Civ 1173, [2012] PTSR 1336,第49段)。船东代表律师关于“为”和“代表”结合使用只能表示TPT代理关系的论点未能令人信服。《航运服务协议》必须结合所述的背景和目的整体解释。协议中多次提及代理,但均指Forests作为出口商代理人的地位,Forests始终被称为“代理人”。如果有意让TPT作为出口商的代理人,却未明确表述,实属令人惊讶的疏漏。
Males勋爵承认,在出口商与TPT之间,出口商在租船合同中拥有经济利益,因为他们需向TPT偿还运费和滞期费,并享有航次收益和洽谈佣金。但Males勋爵不认为这必然表明TPT作为出口商的代理人。这一安排同样可能表明TPT以委托人身份订立合同,但前提是由出口商为其提供实质上的赔偿。此外,尽管出口商需向TPT偿还滞期费,但他们有权根据销售合同向Amrose追回此费用(并需核算航次收益)。至于TPT的账目,即根据新西兰法律编制的未经审计的特殊目的报表,Males勋爵同意法官的观点,在缺乏专家证据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中性因素。
Males勋爵还同意法官的看法,即租船合同签订的时机—在销售合同签订之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TPT并非作为出口商代理人签订租船合同的观点。在租船合同签订时,尚未最终确定将运载哪方的木材,且在某些情况下,出口商未提供满载货物,TPT可自由为其他出口商运送部分货物并自行获利。以COSMOS HARMONY的租船合同为例,可能的装货港是Tauranga,可能装载三家出口商的木材,但也存在新西兰北岛其他装货港的选择,届时可能有不同的托运人。如上所述,TPT签订的许多租约根本不涉及出口商。在这些情况下,如果TPT确实有意作为代理人行事,在签订租船合同时,尚不清楚(如果有的话)哪一家出口商应被视为TPT的委托人。
转向保函,鉴于目前的结论,起点是出口商的论点更优,即TPT以委托人身份签订租船合同。这本身就是得出保函也由TPT以委托人而非出口商代理人身份签发的有力理由。然而,即使这一结论有误,要证明出口商与TPT在保函签发时存在代理关系,需从他们的言行中客观证明双方均同意存在这种关系。Males勋爵认为,出口商的论点更优,即TPT和出口商均未给予此类同意。
关于TPT,船东的代表律师依赖的事实是,TPT在签发保函前曾寻求Forests(据称作为出口商的代理人)的批准,且该批准已获准。但正如法官所述,这可轻易解释为:一旦木材卸货并交付给买方,出口商将失去对货款的担保,尤其在未开立信用证的情况下。尽管TPT不是提单合同的当事人,但在提单通过银行链协商之前,该合同仍为托运人(即Forests作为出口商的代理人)与船东之间的合同,船东有义务凭提单交付木材。因此,若以其他方式交付,取得Forests的同意是合理的。此外,正如出口商代表Mr David Bailey KC所主张的,TPT请求Forests批准并不一定表明其期望Forests(或出口商)在保函被要求支付时提供赔偿。TPT自然会向Amrose寻求赔偿,因为其在同意释放木材前已从Amrose获得背对背保函。因此,TPT的行为并未表明其同意作为出口商的代理人签发保函,且显然不排除其他解释。
至于出口商本身,附件2明确规定,除非遵循附件2规定的程序,即使Forests根据代理协议第5.2.1(c)条款作为出口商的代理人签订租船合同,出口商也不会同意代表其签发保函。更不用说在TPT作为承租人且适用第5.2.1(f)条款时,出口商给予此类同意。Males勋爵不同意船东代表律师为规避Forests实际授权明确限制的两种论点。
关于附件2程序已废弃的建议,正如法官所述,完全是推测。本案已提交大量证据和文件披露,或许比典型管辖权挑战案件更多。但没有合理的证据基础,至少未向法官或上诉法院提及任何内容,表明出口商同意放弃附件2程序。公平地说,船东的代表律师最终未坚持这一论点。
第二论点,关于表面或表见授权,船东的代表律师认为Forests具有代表出口商授权签发保函的表面或表见授权(apparent or ostensible authority),因此应视为具有实际授权。他援引了AJU Remicon Co Ltd v Alida Shipping Co Ltd [2007] EWHC 2246 (Comm) 案。在该案中,原告与被告通过一链经纪人据称签订了租船合同,争议之一是据称代表原告行事的经纪人是否具有授权。副法官(Deputy Judge)在判决中确认了以下原则:
“18. 在我看来,当一名雇员在其表见授权范围内行事,指示经纪人与第三方达成协议,而该经纪人依赖该表见授权行事时,该经纪人具有实际授权达成相关协议。对于经纪人而言,委托人因‘禁反言’(estoppel)无法否认该雇员的授权,因此经纪人获得实际授权。如果在相关时间,Mr Lim不再有权以ATC或AFS的名义租船,但仍保留表见授权,且Mr Kong依赖该授权签订租船合同,则ATC或AFS成为仲裁协议的当事人。”
船东的代表律师主张,Forests具有代表出口商授权签发保函的表见授权,因此出口商因禁反言无法否认Forests的授权,结果是Forests获得实际授权,允许TPT签发函。
Males勋爵认为首先需考虑的问题是,这一在上诉前未在下级法院提出的论点,是否可在本法院提出。关于在审判后上诉中提出新论点的原则,最近在The Dijilah [2024] EWCA Civ 580案中有详细阐述,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临时上诉(参见Rana v Ealing London Borough Council [2018] EWCA Civ 2074案。这些原则包括,若新论点未在下级法院提出,且存在合理可能性表明若当时提出该论点,可能已提交影响结果的证据,则通常不允许提出该新论点。
Males勋爵不允许提出这一新论点。从Chambers法官的表述可知,该原则依赖于禁反言的运作,而禁反言需证明存在表明授权的行为,委托人向第三方声称(holding out)和依赖(reliance)。本案中,未在证据中探讨Forests是否具有区别于实际授权的表见授权,以及TPT是否依赖该表见授权。若该论点已提出,特别是考虑到Forests作为管辖权挑战申请的当事人;如果是这样,证据中未涉及TPT是否依赖表面权限(ostensible authority)的问题。Males勋爵任务现在允许提出这一论点是不公平的,因为Forests已成功挑战管辖权,且不再是本诉讼的当事人
但即使允许提出这一新论点,Males勋爵认为认为,如船东代表律师所主张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论点,至少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没有证据显示TPT依赖出口商对Forests的任何表明授权行为。虽然如前所述,这可因该论点未在下级法院提出而解释,但事实是,缺乏此类证据,案件的关键要素缺失。若允许案件继续进行,是否能填补这一证据空白完全是推测。
第二,隐名代理人的责任仅在代理人具有实际授权代表委托人订立合同时产生。隐名代理人原则已属异常,不应扩展至AJU Remicon案所述的因禁反言产生的虚构实际授权。该案并非隐名代理人的案件,而是代理人据称代表委托人行事的案件。无需决定Chambers法官所述情况下称代理人因禁反言获得实际授权是否正确。仅需指出,该原则不适用于隐名代理人的案件。
第三,正如Sumption勋爵在Playboy Club London Ltd v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SpA案中所解释,他将未,隐名代理人规则描述为“18世纪和19世纪法学的异常遗产,因其古老而非连贯性在现代法律中存续”,隐名代理人与第三方之间关系的一个特点是其互惠性:
“15. A与B的隐名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可能非基于同意,但至少是互惠的。隐名代理人不仅可起诉,还可被诉于合同。A可选择起诉代理人。若隐名代理人起诉A,A可提出对B可用的任何抗辩。”
在缺乏真正实际授权、通过禁反言创造虚构实际授权的情况下,这一互惠性将缺失。这意味着被禁反言的一方将对合同负责(这是船东寻求实现的目标),但无法依合同起诉,因为其无法依赖对自己不利的禁反言来确立诉因。
基于上述理由,Males勋爵认为出口商的论点更优,即他们作为隐名代理人不对保函负责;因此,驳回船东的上诉。
该案的情况和Yangtze Navigation (Asia) Co Ltd & Anor v TPT Shipping Ltd & Ors (The Xing Zhi Hai) [2024] EWHC 2371 (Comm)案类似,只是船东不同。涉及提供保函及出口商都是一伙,所以很大概率是有预谋,或者说对方所起草的各自委托、代理协议的文书非常严谨,应该是有顶尖的律师来起草。作为船东或者OP公司,最好都去认真看看当事人拟定的协议,避免踩坑。
在The Xing Zhi Hai这个案中,关于隐名代理人规则的法律适用,Christopher Hancock KC法官认为相关法律原则在本案事实应用上几乎没有争议。首先引用枢密院在Siu Yin Kwan v Eastern Insurance Co Ltd [1994] AC 199案, 第207页的判决,其中Lloyd勋爵阐述如下:
(1) 隐名代理人可就其代理人在实际权限范围内代表其订立的合同起诉或被起诉。
(2) 代理人在订立合同时必须有意代表委托人行事。
(3) 隐名代理人的代理人也可就合同起诉或被起诉。
(4) 第三方对代理人可用的任何抗辩同样适用于其委托人。
(5) 合同条款可通过明确或暗示方式排除委托人起诉或被起诉的权利。合同本身或订立合同的周边情形可能表明代理人是真正的唯一委托人。
其次,最高法院Playboy Club v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SpA [2018] 1 WLR 4041案中,Sumption勋爵引用上述五项测试,并补充第六项:第三方必须不可撤销地选择是否起诉代理人或隐名代理人。Lloyd勋爵在Siu Yin Kwan v Eastern Insurance Co Ltd [1994] AC 199案中进一步指出:“如果法院过于轻易地解释书面合同为否定隐名代理人介入的权利,将大大破坏Diplock勋爵在Teheran-Europe中提及的商业案例中的有利推定。”
Christopher Hancock KC法官在这个案中,接受上述陈述为该项法律的准确表述。
相反,所谓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而实施代理行为,如果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的成立,要求相对人必须是善意且无过失。表见代理最重要的特征是相对人有正当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不问本人是否有过错。代理人伪造或盗用本人的授权委托书,并将其提示于第三人,从而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不构成表见代理。在表见代理中,判断相对人是否为善意且无过失的时间点,因积极代理和消极代理而有不同。在表见代理中,相对人既可主张狭义无权代理,向无权代理人追究责任;也可以主张成立表见代理,向被代理人追究责任。但二者只能选择其一,不得同时主张。构成表见代理,须在代理行为实施过程中存在表见行为。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对自己的主观善意承担举证责任,判断相对人的举证是否充分,应当在个案中据实判断。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要情形。因表见代理成立,被代理人承担责任后,其因履行合同遭受损失的,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但应限于直接损失和财产性损失。
海运圈聚焦专栏作者Alex (微信公众号 航运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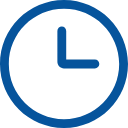 2025-08-06
2025-08-06 648
648 














